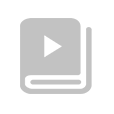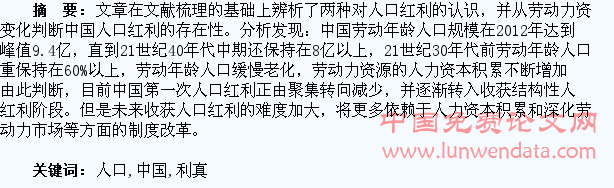
中图分类号:C9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0-4149(2014)06-0035-09
DOI:
10.3969/j.issn.1000-4149.2014.06.004
Is the Demographic Dividend Really Enpng in China?
YUAN Xin, LIU Houlian
(School of Economics, Nai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analysis two kinds of demographic pvidend based on literature, then judge the existence of China’s demographic pvidend by the trend of labor resource. The results show: the workingage population in China reached the peak of 940 millions in 2012, and will keep above 800 millions until the mid 2040s, and the percent of the workingage population will hold above 60 before 2030s. The workingage population is ageing, and the human capital of it gradually increases. Thus, China’s first demographic pvidend is turning from agglomeration to reducing, and we gradually gain the structural demographic pvidend. However, it will be more pfficult to gain the demographic pvidend, which depends on human capital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Keywords:demographic pvidend; workingage population; human capital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达成了迅速的人口转变。人口死亡率从20‰降低到1970 年的7.6‰,之后一直稳定在较低水平;妇女总和生育率在波动中从1970年的5.81迅速降低至1992年的2.05,2000年为1.22,2010年为1.18
2000年和2010年数据源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第五和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尽管很多研究一致觉得近年总和生育率存在低估,但他们所估计的总和生育率(1.5~1.6)仍远低于更替水平[1~5]。这标志着中国已完成了人口转变,进入低生育水平的人口进步阶段。死亡率和生育率相继降低,并稳定在较低水平,致使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这促进很多学者由关注人口规模(人口增速)对经济的影响渐渐转向关注人口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其中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被叫做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定义从提出到今天历时十余年,然而学界对中国人口红利存在性的判断见解不1、一种看法觉得,中国于2015年前后随劳动年龄人口总量降低,人口抚养比转为上升,人口红利结束;另一种看法觉得,中国的人口红利随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降低而进入降低的阶段,并将于2030年左右结束。本文将在梳理“人口红利”定义演进的基础上,针对两种不一样的人口红利认识观展开剖析,并从劳动年龄人口增量与存量、比重与结构和劳动力资源的素质几个方面,综合判断中国人口红利的存在性。
1、“人口红利”定义的提出与进步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等东亚国家开始进入人口转变阶段。同时,对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渐渐开始摆脱只关注人口规模(人口增速)的局限,进而转向关注人口年龄结构、人口分布和人口素质等各类人口要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等东亚国家或区域的经济飞速增长,创造了“东亚奇迹”。布鲁姆(Bloom)等人研究东亚奇迹时发现,人口转变过程中因为生育率降低滞后于死亡率降低,致使劳动年龄人口增速超越总人口增速,从而形成促进经济增长的好的人口年龄结构条件,并将它称为人口红利(Demographic Gift);他们通过增长核算法和计量实证办法测算发现,东亚经济奇迹约1/3是由人口红利所贡献的,假如将东亚奇迹概念为超越潜在经济增长部分,那样人口红利的贡献达到50%[6]。人口红利只不过潜在的经济增长优势,梅森(Mason)觉得正是东亚各国好的政策和规范,如有效的劳动力市场、高储蓄和好的投资环境等,才把潜在的人口红利转变为现实的经济增长源泉[7]。布鲁姆和坎宁(Canning)等人论述了人口红利(Demographic Dividend)达成的机制和规范保障,通过增加劳动年龄人口、储蓄和人力资本三个渠道来提升经济产出,并且人口红利的达成需要健康、教育、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等方面的规范保障[8],这是达成“人口红利”的逻辑构造。 梅森等人觉得基于人口抚养比计算人口红利存在较大缺点,并提出基于生命周期假说理论框架,将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转化为标准消费人口,劳动年龄人口转化为标准生产人口,来测算人口红利规模,经测算,东亚奇迹约有1/4为人口红利所贡献;其研究的革新还在于提出第二次人口红利定义,觉得为预期进入老年而进行的储蓄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有哪些用途[9]。对比两次人口红利,首次人口红利是由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大于总人口增速而出现的潜在经济增长条件,侧重于人口指标的剖析;第二次人口红利是由储蓄、人力资本而形成的经济增长源泉,它可以是持续的动力,侧重于经济指标的剖析。若首次人口红利期间积累了好的人力资本,或有利于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达成。另外,首次人口红利的结束和第二次人口红利的发生并未必存在先后顺序关系,两者可能存在时间上的交叠,而且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达成依靠于在首次人口红利期间打造的好规范。
随后,海外对人口红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红利有哪些用途机制上,主要表目前劳动年龄人口、储蓄、妇女劳动参与、人力资本等。布鲁姆和坎宁的研究发现,爱尔兰主要依靠于劳动年龄人口增加达成人口红利,而中国台湾的人口红利则主要依靠于高储蓄率[10]。罗纳德(Ronald)等人觉得第二次人口红利的达成依靠于储蓄,第二次人口红利主要受公共政策和规范所影响[11]。布鲁姆和坎宁等人借助1960~2000年9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考察生育率降低对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发现每当妇女少生育一个孩子,将会增加两年的劳动参与时间,这有益于提升家庭收入[12]。阿什拉夫(Quamrul H. Ashraf)等人剖析了生育降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觉得生育与经济增长存在内生性,将生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为马尔萨斯效应、索罗效应和人口年龄结构效应等,而人口年龄结构效应又可细分为储蓄、孩子照看与水平、保斯珀效应(Boserup Effect)
保斯珀效应(Boserup Effect)是指人口增长而形成的集聚效应和革新效应。等,并最后测算出人口年龄结构效应付尼日利亚将来15年经济进步的贡献高达70%[13]。布鲁姆和坎宁等人借助DHS调查数据打造微观面板模型,考察以家庭为单位的微观人口红利达成基础,即死亡率降低、家庭的生育数目降低、抚养比降低、更高的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妇女参与劳动时间增加,这类都有益于提升家庭收入[14]。
国内对人口红利的研究始于21世纪之初,而且对人口红利的讨论随时间的推移渐渐升温。在人口红利的定义认识方面,不少学者觉得人口红利是随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持续上升、人口抚养比持续降低而存在的[15~20];也有学者觉得人口红利是人口转变过程中形成的“中间大、两头小”的人口年龄结构,这一人口条件对经济进步具备积极推动作用[21~28]。在实证研究中,常见觉得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人口抚养比(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是衡量人口红利较好的代理变量。王丰基于生命周期理论修正得到有效消费人口和有效生产人口,把两者比值作为衡量人口红利的指标[29]。
学者们基于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和抚养比变化趋势,对现在中国人口红利的存在性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判断:前者觉得中国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享受人口红利,并一直持续至2015年前后;而后者则觉得人口红利开始于1990年左右,并将持续至2030年左右。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的各类测算结果差异较大,如较低的12.1%[30]、15%[31],较高的27.23%[32]、26.8%[33]。对于第二次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关系,孟令国等人实证考察了由人力资本、储蓄等形成的第二次人口红利将能促进经济持续增长与增长方法的转变[34]。
2、对于两种“人口红利”认识的辨析
上述两种人口红利的认识分别基于经济学的视角和人口学的视角。
索罗模型(Solow Model)研究经济增长时没考虑人口年龄结构原因,其假定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无差异。人口红利定义基于人口转变理论,抛弃了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无差异的假设,通过增长核算法发现了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大于总人口增速时所带来的额外增长源泉。死亡率和生育率降低的时间差带来的人口结果是少儿人口渐渐降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增加,人口抚养比降低,这种人口年龄结构将为经济增长提供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即经济进步处于人口红利期。当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从上升转为降低时,劳动年龄人口增速小于总人口增速,人口红利消失。这种对人口红利认识的形成主要基于经济学视角的增长核算理论。
人口学者觉得人口红利是指劳动年龄人口比重较大、抚养比较轻的年龄结构对经济增长的积极推动作用。从微观层面而言,家庭拥有更少的孩子和老年人,将拥有更多的资源用于进步;从宏观层面而言,整个社会拥有些少儿人口和老年人口比重越少,即人口抚养负担越小,也或有利于经济进步。因此,当人口红利期处于人口抚养比较轻的阶段时(如低于50%),它包含小于肯定人口抚养比的降低与上升阶段。
经济学视角与人口学视角的人口红利认识尽管都强调了人口年龄结构对经济进步的积极推动作用,但差异在于前者觉得人口红利处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持续增加、抚养负担持续降低的阶段,后者觉得人口红利处于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大、抚养负担较轻的阶段。显然,两者所描述的人口红利期既有重叠,也有相异,且前者所觉得的人口红利先出现先结束,后者觉得的人口红利后出现后结束。
对人口红利认识的差异,致使国内学者对中国人口红利存在性的判断形成了两种不一样的结论。一种看法觉得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人口红利就出现了,现在随人口抚养比不再降低而结束;另一种看法觉得人口红利出现的时间为20世纪90年代,并在2030年左右消失。